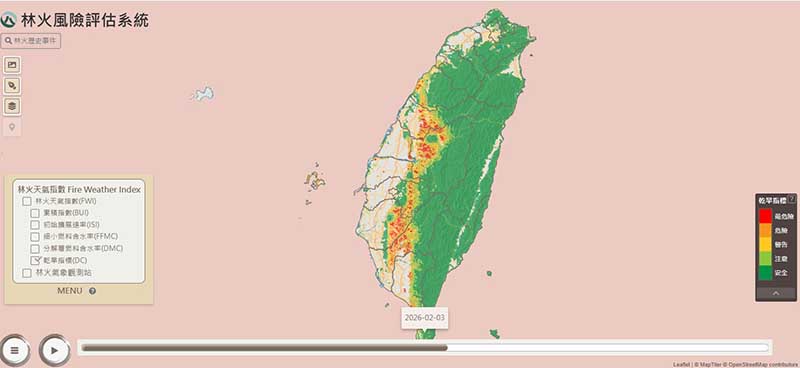MONTHLY ADMONITION NEWS



WORLD CHINESE JOURNALISTS
白嗣宏追憶愛妻:我永遠的“美的精靈”
來源:上海市歐美同學會留蘇分會 / 白嗣宏
|
記者/作家:編輯
|
發佈時間 :2020-11-20
|
728 次瀏覽:
|
分享到:
憶愛妻奧麗佳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白嗣宏,1937年生。上海市東中學畢業,1956-1961留蘇,畢業于列寧格勒大學語言文學系。作家、翻譯家、文化學者。俄中文化交流協會主席。
攜手59年10個月之後,2020年10月18日,愛妻奧麗佳撤手而去,祝她早上天堂。她受過聖洗,上帝必將眷顧她,使她在天堂有個快樂的生活。我們一起為保衛愛的權利,犧牲了一切,但得到了人間的溫暖,成就了我們坎坷而豐富的一生。

浪漫的聖彼德堡
邂逅
1959年三八婦女節,列寧格勒大學語言文學系和東方系組織了一次兩系同學的聯歡舞會。我與同班中國留蘇生吳元邁同學有幸參加。在舞會上我突然發現一位全身洋溢著非同一般的雅致嫻淑貴族氣質的姑娘。
她身材苗條均稱,白白淨淨的臉盤上,一雙深灰色的眼睛流出淡淡的笑意,你若陷入就自拔不出。更引人的是她那厚度適中卻豔如紅玫瑰的雙唇,竟是自然的造化,無需唇膏添色。長長的脖頸,稍稍前傾,顯出一股大家閨秀的微微傲氣。一襲黑色平口露肩的旗袍裙,裹住雕塑家夢想的形體。一串紅珊瑚的中長項鍊,盤在黑裙領口下,配上尖頭半高的船鞋,宛如俄國十九世紀傑出畫家克拉姆斯科依《無名女郎》的現代版,從特列季亞科夫畫廊來到了舞會上。優雅,清亮,真是天仙下凡。“宛如瞬息即逝的夢幻,宛如清純美麗的精靈。”(普希金《致凱恩》)
一生追求美的我,自然覺得是上蒼給的機會。我就在下一輪舞中邀請她共舞一曲,竟然得到她的熱情回應,實在幸運。

1956年6月,上海市東中學留蘇預備生在北京俄語學院,前排右二為作者

1957年夏,國際青年聯歡節,右三為奧麗佳

大學時期的奧麗佳(左二)
初會
不久,我又有了一次目睹“美的精靈”的機會。那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語文系和東方系的學生們在教學樓前的涅瓦河濱集合排隊,參加節日遊行活動。我拍攝的一幅照片裡,背景上隱約可見那位美麗的精靈。遊行結束後大家回到各自的宿舍。令我感到特別激動的是她竟然和我同住一幢宿舍樓,就是屹立在涅瓦河邊的大樓。旁邊是彼得保羅要塞,對面是冬宮。年年夏天最美麗的涅瓦河,多少花季少年淑女或打情賣俏,或竊竊私語,整個列寧格勒沉浸在愛的夢幻裡。

這是1959年五一節集合遊行的照片。作者就是拿著這張照片第一次約會去的。當中的女孩他以為是奧麗佳,結果不是。但這張照片決定了他們的一生

作者(右一)與蘇聯同學的合影
定情
有一次一起讀抒情詩的時候,奧麗佳從小把普希金的詩讀得滾瓜爛熟,能大段大段吟詠《葉甫根尼•奧涅金》。她喜歡泰戈爾、彭斯、葉賽寧的詩。有些詩是我們共同的愛好。例如,彭斯的詩《我的愛人像一朵紅紅的玫瑰》(英文):
A RED, RED ROSE
O My luve is like a red , red rose,
That’s newly sprung in June;
O my luve is like the melodie,
That’s sweetly played in tune.
我的愛人像一朵紅紅的玫瑰,
燦燦然在六月裡初開;
哦,我的愛人像一曲美妙的旋律,
曼曼地演奏是那樣的甜蜜。
As fair thou art, my bonie lass,
So deep in luve am I;
An I will luve thee still, my dear,
Till a’ the seas gang dry.
你是如此美好,心愛的人兒,
我呀,深深地愛著你!
親愛的,我永遠愛你,
縱使大海乾枯滴水流盡!
Till a’ the sea gang dry, my dear,
And the rock melt wi’ the sun;
And I will luve thee still, my dear,
While the sands o’ life shall run.
縱使大海乾枯滴水流盡,
岩石也被太陽燒成灰燼!
親愛的,我仍然愛著你,
只要我生命猶存熱血未盡!
And fare thee weel, my only luve,
And fare thee weel a while;
And I will come again, my luve,
Tho’s it were ten thousand mile!
道一聲珍重,我唯一的愛人!
你要珍重,當我們暫時離別!
我一定會回來,我的愛人,
哪怕遠隔千里萬里!

這首詩我們在森林公園大聲朗誦,在花徑小道淺唱吟哦,融入我們年輕的熱血裡,融入我們沸騰的青春裡!我們一致決定,這就是我們的定情詩。2005年,我們攜手暢遊愛丁堡,專門去憑弔彭斯的紀念雕像,感謝他陪伴我們多災多難又幸福的人生。在此後坎坷的生命之路上,是它給了我們力量,是它給了我們不受任何外力的影響,戰勝了一切障礙,捍衛了我們愛的權利。
團聚
1961年6月留學結束,我接到通知回國,從列寧格勒集體到達莫斯科,住進大使館招待所。事出突然,奧麗佳遠在中來亞杜桑貝市工作,她飛來莫斯科見面,並一同去使館請求辦理她隨我回國的簽證。答覆是只能由我先回國,分配工作後再按有關手續辦理。我回國後,因為有了這層海外關係,工作分配受到限制,最後分配到安徽藝術學院。無獨有偶。奧麗佳也是因為有了我這層中國丈夫的關係,無法留在莫斯科工作,儘管有單位需要。

1961年6月,白嗣宏離開莫斯科回國前與奧麗佳的合影。而再次團聚是三年後
1961 年11 月初,幾經周折,我被分配到安徽工作。到達合肥,到校報到後,我即提出安排妻子來華團聚與安排工作的事。校人事處說,這事要省裡解決。從此我就開始了漫長的爭取家庭團聚的艱苦歷程。我到合肥市公安局一科遞交申請書。公安人員說,等有關部門批下來後,我們通知你。申請如石沉大海,沒有任何消息。我不斷去問,得到的答覆總是沒批下來,還要等。“等”的心情,大家都體驗過,個中的心理精神負擔,只有當事人瞭解。但我們從未放棄團聚的期望,一直互相支持,互相安慰。
我當時有一些出差去北京的機會,每次去北京,必去長安街上的公安部打卡。每次都是同一位官員接待。每一次的答覆都是“再等等”。那時中蘇關係已經破裂,希望渺茫。但是我們的愛卻沒有因為受阻而淡化,反而更加堅貞,更加強烈。我們在被迫分居期間,以信函當使者,傳送愛情和問候,思念和鼓勵。我們之間的信有兩百多封。我們同在蘇聯時期的信和我從中國寫給她的信,都由她母親妥為保存,日後交給了我們。而她寫給我到中國的信,卻在文革中被迫付之一炬。
等了兩年多以後,只有最後一條路可以一試。奧麗佳鼓起勇氣,給我國中央領導寫了一封人民來信。幸運的是,這封信得到了批示。有關部門得到指示,同意她來華定居。安徽藝術學院的黨委書記對我很是關心也很同情,把我找去,說是省委批下來了。你去辦手續吧。市公安局的官員把一個樣本給我,要求當場照樣寫一份申請妻子來華定居的申請書。10月她收到通知,可以去中國駐莫斯科大使館領事部辦理定居簽證。

奧麗佳(攝於1961年)
1964年4月,奧麗佳乘坐火車到達北京。那時我已經轉入合肥師範學院藝術系,再轉外語系。經學校批准,我去北京接她。許多在北京的熟人中,時任中國紅十字總會的黨委彭書記和夫人,一起到我們住的東安旅社來見她,安慰她說, 在中國也是一樣,歡迎她來中國參加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她聽了之後非常感動,一到北京就有朋友這樣體貼理解她。
我們在北京有許多老同學,聽說她到了,大家都來見面。我們請兩位老同學到王府井老的東來順小聚。也到老同學吳元邁學部委員家裡做客。我們在北京,沉浸在團聚的幸福之中。在北京住了幾天。一次在遊覽頤和園時巧遇鄒厚功教授。他夫人也是蘇聯姑娘,一見如故。他們夫婦邀請我們到家做客,見到兩位小朋友,其中一位就是鄒傳華。我們從他們那裡瞭解到一些中蘇跨國婚姻的情況和生活常識,為此十分感謝他們一家。離開北京,我們坐上了去合肥的火車。
合肥
北京到合肥沒有直達火車,需要在蚌埠轉車。當地政府的接待科派人接車並安排在賓館休息一晚,第二天再走。她一方面對受到的接待表示感謝,另一方面也見到了中國的真實生活。
當時中國和蘇聯相比,生活條件有著相當大的差距。到校之後,才知道安排了一套二室的房子。學校的木工給打了一架雙人床。簡樸的公家傢俱、煤球爐、瓦罐燒水壺,都沒有難倒她。就連煤球餘下的碎煤再做煤球的本事,她也學到了手。能與自己心愛的人一起生活,就是最大的幸福。我們的住所,在學校旁門附近,門外是農田。一個不大的藕塘,每年夏天荷花盛開,她感到特別親切。這與她所學專業很有關係。她學過梵文,瞭解佛教藝術,特別喜愛敦煌的藝術珍品。在她看來,荷花就是佛教精神的象徵。有了兒子之後,我們時常帶著他到荷花塘邊久坐,吸取荷花的精氣,鼓勵我們在愛的道路上走下去。
在那個特殊時期,各地俄語教學處於下坡路。但是全國各地還有一些。安徽就有三所大學招收俄語專業的學生。官方已經不聘請蘇聯教師,而和中國留學生結婚來華的蘇聯人也不斷減少。合肥工業大學原來就有一位,於1963年離開中國。她回國前對我說,我會告訴你妻子,要做好準備。

合肥師範學院
在安排奧麗佳工作時,還有一個小插曲。省委有關部門在討論時擬安排在安徽大學。合肥師範學院則近水樓臺,說她丈夫就是我們學校的,應首先考慮我們學校,力爭而得。到校後不久,奧麗佳開始教學工作。年輕美麗、活潑親和的奧麗佳老師得到學生們一致好評。教學給她的生活增添了很大的活力。雖說物質條件不那麼理想,也沒有成為問題。1964屆的畢業生仍然懷念她,後來還有學生專程到莫斯科來看望她。
1964 年暑假很快來臨。合肥師範學院院長在省委有一定的分量,同省政府辦公廳說好,安排暑期去黃山度假。那時她已經有了三個多月的身孕,醫生說沒問題。我們先坐火車到蕪湖。第二天有一位廳長的專車去黃山,順便把我們帶到了黃山。黃山管理處把我們安排到溫泉邊的黃山賓館。
那時我們都不到三十歲,相持登上天都峰,險走鯽魚背。沿途的如畫風景,在她的眼中,就是一幅幅啟動的印象派美圖,無時無刻不發出讚歎。到了玉屏樓,住了一晚,再繼續登山,到了北海賓館。那時遊人不多,很是愜意。接著,我們從黃山去了杭州,住在完全中式的天井型賓館,就在湖邊。對奧麗婭來說是大開眼界。天熱,天井都是窗對窗,赤膊遊客的民主化,實在令人驚歎。蘇堤、斷橋、雷峰塔、蘇小小、岳墳、蘇曼殊墓遺址、弘一法師李叔同……這些人文故事太動人太動人了,給她上了一次中國文化的大課。
從杭州我們回到了上海父母的家。全家熱烈歡迎她的到來。她一進家門就同父母和弟妹們融為一體,孝順父母,親和弟妹。這次到上海,她還見到一些在上海居住的俄國同胞。大家都說這是留蘇學生夫人中最漂亮的一個。對她在那種特殊時代特殊環境中不顧一切前來找丈夫團聚非常欽佩,說不愧是“當代十二月革命党夫人”。

打動奧麗佳的杭州美景
上海給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她對上海的海派文化感到很親切,尋訪俄國僑民文化的蹤跡,也是別有一番情趣。最有趣的是,沙皇俄羅斯最後一任駐上海總領事(1911-1924)維克多∙費奧多羅維奇∙格羅塞(1869-1931)是她母系的曾姨媽艾拉∙帕夫洛夫娜∙裡文(奧麗佳母親的家族)的丈夫。他是現在上海黃浦江畔漂亮的俄國總領事館建築物的建造者,1924年將館址移交給蘇聯政府。他成了上海俄國僑民社團的領導人。去世後埋葬在上海的公墓。奧麗婭為她的先人能給上海留下這樣一幢建築文物十分高興。這裡順便說一下她貴族氣質的源頭。她父系的先人之一是亞∙彼∙奧紮羅夫斯基伯爵,曾任騎兵中將軍長,在庫圖佐夫元帥麾下參加1812年衛國戰爭。他的肖像掛在冬宮1812年衛國戰爭英雄紀念畫廊裡。
1964年十月革命節,是她第一次在國外過節。我們院長特別指示,十月革命節還是要慶祝的。黨委辦公室安排一個座談會,請她參加。會後特別放映一部蘇聯電影。奧麗佳一直記著這位院長的苦心。
1964年12 月,我們的兒子因奧麗婭擦窗而提前出生。我又是長房長孫,我們的兒子白沙也成了長房。我的父母非常高興。兒子是在安徽醫學院附屬醫院出生的,婦產科的聶主任是留蘇的前輩,所以很是順利。外語系的夏雪華老師陪她進的產房。我們為此終身感謝夏老師。
1965年,孩子滿一周歲後,我們打報告給學校,希望1966年暑假她能帶著兒子回國看望母親。1966年寒假期間,系領導通知說,高教部批下來了,暑假期間可以回國兩到三個月。我們把這個好消息通知了她的母親,她的父母都很期望。
可是,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已經山雨欲來風滿樓。系領導再次找她談話說,我們要開展一次政治運動,外籍人員不參加,因此你可按原計劃探親,但是有一個要求,就是運動期間你最好先不要回來,運動結束後你再來。她問,多長時間?系領導答不上來,說是沒確定。她一聽,心情自然難過,擔心回不來了。她懷著沉重但堅決的心情表示,她暫時放棄回國探親,要和丈夫一起。系領導說,那也好,就留下來吧。運動結束後再說。
誰知這場災難竟然持續了十年,到1976 年“四人幫”倒臺時,她已有12年未能探望年紀已老的父母。再次批准探親已經是1980年了,一個獨生女兒16年未能見父母。她苦淚暗咽,為愛情堅持下來。

俄羅斯聯邦駐上海總領館
歲月


1967年8月,夫妻倆上黃山避武鬥,社員幫助挑行李和小兒子
我們沒有參加過任何政治運動,對這種事情只能抱著聽天由命的態度。校園裡大字報鋪天蓋地。外語系也有人寫她的大字報。無名氏揭發,第一條說她否認階級鬥爭。
1971 年合肥師範學院撤銷,外語系併入安徽大學外語系。1972年工農兵上大學。外語系向省革委會報告,說是我們這裡有外教,可以教俄語。學校當年就招了一批工農兵大學生。這批大學生,一部分是高幹子弟,一部分是農民子弟、下放知青。到校後奧麗佳參加了教學工作。青年學生們對她很好,很尊重,也很愛護。我們的兒子更是他們的好朋友 。那時她會說一些中文了,同鄰居交流是她學會中文口語的很好機會。
1974年初。我們有了女兒。她得的癔症在生了女兒之後漸漸消失了。家裡又多了一些歡笑。兒子和女兒相差九歲。工農兵學員們畢業了,卻留下了師生情誼。1975年畢業的第一批畢業生們,于2016年舉行畢業41周年返校活動,當時奧麗佳已經去不了,但她對同學們的友情並沒減少,特別錄了一段視頻發給大會,話語中充滿對學生們的友愛和感激,為他們能在那種政治環境下,對她表現出的大愛精神。今年上海地區的學生們聚會,邀請她參加,誰知已是天人兩隔了。

文革中奧麗佳陪工農兵學員去安徽舒城縣舒城公社開門辦學,與社員合影
希望
1976年, 文革結束了,卻沒有招生的希望,奧麗佳只能到資料室值班。我則重操舊業,寫戲劇和文學論文,翻譯劇本和小說,與安徽文藝出版社合作編輯叢書。奧麗佳給了我很大的支持,家務事她一人擔當起來。每天早上,她先在運動場上跑上一圈,然後回來買大餅油條,買菜,到食堂打飯打菜。
這時我恢復了同安徽文藝界的聯繫,不斷發表作品,同安徽文藝界的朋友相處甚歡。省委宣傳部推薦我出任省文學學會的副秘書長兼外國文學研究會的秘書長。安徽文藝界的領軍人物,如陳登科、江流,都到我們家來做客,奧麗佳設宴招待。著名詩人公劉,作家魯彥周、肖馬、蘇中,都非常關照。最值得一提的是,安徽文聯的胡曉秋先生,是我進入安徽文藝界的引路人。他學俄語出身,是上海外國語學院的畢業生,大氣正派,知識淵博,目光銳利,深孚眾望,退休前任安徽文聯主席黨組書記。曉秋兄朋友遍及全國各地。我參加的一些活動,常常邀請奧麗佳一同參加,她也做出自己的貢獻。撥亂反正之後,中國戲劇家協會編譯介紹中國戲劇文化的小冊子,她應邀把京劇內容翻譯成俄文。
新時期全國各地不斷出版俄蘇文學作品。奧麗佳熟悉俄蘇文學,一些同行們時常來共同探討譯文。她總是有問必答,盡自己的力量協助解答原文理解問題。她對這種探討十分用心,也十分高興,覺得能與大家交流是一大快事。她幾乎成了活辭典。有些是俗語,有些是俄國生活方式裡的用詞,只有熟悉俄國文化風俗的人才能準確理解 ,才能正確翻譯。她自己沒把握的問題,總會想辦法查找資料,使之言之有據。現在翻閱朋友們探討問題和譯文的來信,奧麗佳的形象躍然紙上,栩栩如生。

《阿爾布卓夫戲劇選》中文版
遺憾的是,安徽大學連著幾年不招生,沒學生可教。我們在全國各地的留蘇同學都為我們著急,希望解決我們發揮所長的問題。北京方面有三個單位:北京師範大學、中共中央編譯局和中國國際廣播電臺,但北京戶口懸而未決。從1978年到1987年,十年努力化作泥塵。1988年,在國際廣播電臺工作的學長建議,先借調奧麗佳工作一段時間再說。這樣她就一人獨自前往北京工作。電臺說他們不受戶口限制,由專家局特批。借用期間考察合格,提出安排工資380元。
這時我已得到蘇聯新聞社的邀請,去莫斯科工作。我們作出決定,接受聘請出國工作。出國之前,我們回上海探望父親和弟妹們。也專門拜訪我們敬重的草嬰師。80年代,我們多次到上海,每次都得到草嬰師和天民師的熱情款待,鼓勵和支持。他聽說我們決定出國後,十分感慨。1988年10 月國慶之後,我們到了莫斯科。

1988年10月2日,白嗣宏與奧麗佳在赴蘇的飛機上
歸去
我到了莫斯科之後,立即按照合同,享受外國專家待遇。工資中的四分之一為外匯。那時蘇聯正是戈巴契夫推行改革之際,新思維和公開性,與早期中國的改革有些相似,但畢竟國情不同,各有各的路。我到後才瞭解到,蘇共正在為恢復中蘇正常關係做輿論準備,需要翻譯編輯大量中文資料,我的到來,恰逢其時。莫斯科本地的中文譯者交新聞社出版的,都經過我的手。中文編輯部還約我譯過一些單行本,在一年多時間裡我正式署名出版了三本譯著。
奧麗佳回國後,因當時去中國是定居,辭去了工作。這次回國,需重新安排。經多方聯繫,她回到了蘇聯科學院系統工作,做到首席館員。她到了科學院圖書館工作以後,和大家關係處得很好,擔任採編組組長,直到2001 年退休。我除了本職工作外,文學研究和翻譯仍在繼續,作品在國內不斷出版發表。意外的是,在莫斯科又見到了老友鄒厚功教授。我們熱心華人社團工作,在他的倡議和贊助下,一起創建了莫斯科華僑華人聯合會。我另外還參與了國際經濟家協會的早期工作,負責亞洲事務,曾任監委會主任。在我75 歲時,被國際經濟家協會列為協會精英。

蘇聯(俄羅斯聯邦)科學院
在俄羅斯和世界各國經濟學界一年一度的年會上,我有機會結識不少政府領導官員和學者。中俄文化交流工作一直不斷,涉及戲劇,電影,文學。同俄中友協的合作項目很多,因而被推選為中央理事會常務理事。這些社會工作的後盾,就是奧麗佳。家務事全部由她擔當起來,使我有精力和時間做這些工作。
我們結婚59年10個月,經歷了中蘇友好、中蘇敵對、中俄戰略夥伴等階段,風風雨雨,我們的家庭,都是因為奧麗佳的美麗心靈和她的大愛,才支撐下來。我們堅信,中俄友好才是人間正道。像我們這種中俄跨國婚姻,同兩國的關係緊密相聯。中蘇交惡,我們受罪。中俄友好,我們得益。要保持這種婚姻的長久,就要對彼此的文化包容,互相補充互相豐富。
奧麗佳唯一的短錄影,就是給學生們的致辭。她說,我們家洋溢著對中國的友好感情。這是她的臨別贈言。
為紀念她,這美的精靈,特書此文,以告慰她的在天之靈。
白嗣宏 泣書
2020年11月1日
於莫斯科
作者 | 白嗣宏
圖片 | 白嗣巨集、網路
主編 | 邵甯
編輯 | 于沛欣(特邀)
-
陪伴移工迎新年安心轉職!中彰投分署114年成功媒合逾2,000名移工銜接新雇主
2026-02-13
-
2026-02-13
-
思索人與自然共生的可能 科博館植物園推出《野地之詩-臺灣原生草花的棲地記憶》特展
2026-02-12
-
邁向新階段農業學術研究與人才培育合作 興大與農業試驗所簽訂(MOU)
2026-02-13
-
2026-02-12
-
農曆年節送禮不煩惱 工策會官方認證「臺中市十大伴手禮」市民安心選擇
2026-02-11
-
創世「第36屆寒士吃飽30 送禮到家」公益行動讓凜冽寒冬充滿愛的味道
2026-02-11
-
開創醫療檢測與精準分析的里程碑 興大奈米團隊獲得日本光電大廠高度肯定
2026-02-11
-
臺灣高等教育資源共享與區域均衡發展上邁入新階段 國立大學系統擴大至15校
2026-02-10
-
助600位弱勢新住民二代翻轉未來 賽珍珠基金會「童心協力」圍爐20年愛不間斷
2026-02-10
最 新 資 訊
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