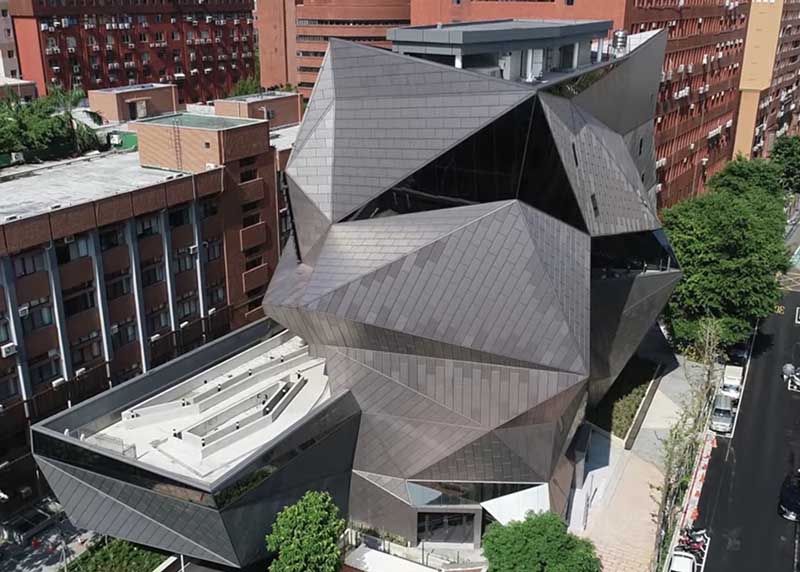WORLD CHINESE JOURNALISTS
白宮直播了一場舉世矚目的美烏簽約外交劇如同棱鏡一般,將國際政治光譜折射成有點荒誕的彩虹。本是雙方磋商議定好程式的簽約發佈會,卻被澤連斯基悲情英雄式的情緒管控失當,演化引發了國際風雲一波三折的瞬時變幻。他的衣著手勢和激情語言,都在表達他對烏克蘭的主權與尊嚴的堅守,“政治就是永不落幕的即興劇”。
莫斯科劇院排演諷刺澤連斯基的先鋒戲劇,而基輔地鐵深處的某個孩子,正用蠟筆在防空洞牆面塗抹——藍黃色火焰吞噬黑色巨龍,右下角歪斜地寫著:“我們的總統會吼死他們”。 當澤連斯基被P成揮拳的卡通形象開始流傳,世界忽然意識到:這個曾用演技拯救國家的演員,正在用失控的真實性解構後現代政治的劇本規則。“當獨幕劇撞破第四面牆,觀眾席與舞臺終將同葬於瓦礫。”
一場失敗的簽約外交,讓澤連斯基又一次置身懸崖邊上。
逆風執炬,暗夜啟明
在 2022 年春的陰霾裏,基輔的鐘聲於硝煙中顫慄。彼時,一個身著軍綠 T 恤的身姿,似絕壁蒼松,傲然挺立。他將國徽別於胸口,那一抹莊重,宛如把星辰種入荒蕪的暗夜。往昔,他是螢幕之上的喜劇王者,於歡笑與詼諧間穿梭;今朝,卻在歷史的凜凜刀鋒上翩然起舞。
他的誓言,似金石擲地,鏗鏘有力,穿透恐懼的重重陰霾——“我需要彈藥,不是順風車”。那話語,仿若熾熱的火種,點燃了這座城市不屈的靈魂。基輔的燈火,在戰火中倔強地燃燒,皆因他的眼眸深處,跳躍著永不言棄的烈烈火焰。
廢墟之上,他以破碎的磚瓦為素箋,用軍民的血淚作墨汁,書寫著一部宏偉史詩。西方政要的掌聲,於他而言,不過是虛幻的迴響。他的目光,始終緊緊凝視著第聶伯河畔那片焦土,恰似荷馬凝視著特洛伊的殘垣斷壁,滿含悲憫與堅毅。
那些將他譏為“棋子”的言語,在他與士兵同處戰壕、共用粗簡晚餐的煙火氣息中,消散如煙。世人只看到鎂光燈下他筆挺的西裝革履,卻不知在每一個深沉的夜晚,他輕撫陣亡名單時,指尖所觸碰的,是那些尚未冷卻的生命溫度,那是無盡的悲痛與責任。
語言鑄盾,詞韻凝光
他的聲音,宛如席捲洲際的磅礴颶風,跨越山海,直擊人心。在國會山那宏偉的穹頂之下,他讓《珍珠港》的經典臺詞重煥生機,似古老的歌謠在新時代奏響激昂樂章;於歐盟的圓桌之前,他以索福克勒斯式的悲劇感染力,喚醒了沉睡在眾人心中的良知。
當那句“這可能是你們最後一次看見活著的我”從他口中說出,古希臘英雄的悲壯宿命與現代政治的複雜博弈,在他身上達成了一種奇妙而不可思議的和解。
有人嘲笑他不過是弄權的戲子,卻不知在戰情室的沙盤之前,他將莎士比亞的獨白幻化為精妙的戰術推演密碼。那些被視作“表演”的演講,實則是一場用詩性重構殘酷現實的神奇煉金術。當他佇立在布查的殘垣廢墟之間,那一刻的沉默,比任何華麗的修辭都更具震撼力,如洪鐘巨響,振聾發聵。
正如拜倫在希臘獨立戰爭中實現精神的覺醒,澤連斯基以行動有力地證明:真正卓越的政治家,本就是那最高明的詩人,用言語的力量,為國家與人民築起堅固的堡壘。
破鏡自證,浴火重生
命運,給予他一個荒誕而又深刻的隱喻。曾經在電視劇中飾演總統的演員,如今在現實的舞臺上,接過了遠比劇本更為殘酷的權杖。當俄軍的坦克轟鳴著碾過國境線,全世界都在暗自揣測,等待著“加尼式逃亡”的續集上演。然而,他卻決然地撕碎了預設的劇本。
在總統府的走廊,他掛滿了陣亡將士的相框。那些定格的面容,是戰爭的傷痛,亦是國家的脊樑。面對質疑他缺乏政治經驗的聲浪,他以推動軍事現代化改革的雷霆手段予以回應。
他如同米開朗基羅雕琢《大衛》一般,精心重塑國家機器。將亞速營的極端分子納入正規軍序列,恰似但丁把惡魔巧妙地寫入《神曲》,在複雜中尋求秩序;在歐盟的殿堂中討要入場券時,他又化身為伊拉斯謨式的人文主義者,以智慧與溫情打動人心。曾經那具被稱作“政治素人”的軀體,在戰爭的熊熊熔爐中,正逐漸淬煉出如馬基雅維利般堅韌的鋼骨。
星鏈領航,奧德賽行
當克裡姆林宮的導彈劃破如墨的夜空,他的推特帳號,宛如一座永不沉沒的希望方舟。每一條動態,都是射向輿論戰場的銳利箭矢;每場視頻演講,都在悄然重構著賽博空間的戰爭法則。西方的政客們驚歎於這位“手機總統”所擁有的神奇魔力,他精准地把握著 TikTok 時代的注意力經濟,將其巧妙轉化為國際援助的精確制導武器。
在哈爾科夫那滿目瘡痍的廢墟之中,他開啟直播,生動地示範著何為數字時代的城邦守護者。他用 Zoom 會議凝聚起流亡的議會,以加密通訊指揮著敵後的特工,甚至促使戰場無人機操作員與矽穀的工程師結成跨國兄弟連。當他說出“現代戰爭是數學與勇氣的乘積”,那一刻,雅典學院的智慧門徒與烏克蘭草原上的豪邁哥薩克,在他身上完成了一場跨越時空的靈魂對話。
苦難共情,掌心山河
他的手掌,永遠留存著戰地泥土的質樸顆粒。與那些躲在防空洞的官僚截然不同,他堅持每月親赴前線。在巴赫穆特的掩體之中,他與士兵們一同分食粗糙的黑麵包,那簡單的食物,傳遞著生死與共的情誼;在敖德薩的醫院裏,他輕輕撫摸著截肢少年的繃帶,那溫柔的動作,飽含著無盡的疼惜。
當西方記者追問戰略得失之時,他默默蹲下身,為一位老婦人系緊散落的頭巾。這一溫情的舉動,被基輔的畫家精心繪製成新的聖母像,成為人性光輝的永恆定格。
那些無端攻擊他“利用平民苦難”的指控,在馬裡烏波爾疏散通道開通的那一刻,便如泡沫般不攻自破。當他抱著失去雙親的孤兒緩緩走過檢查站,赫拉克勒斯十二試煉的古老神話,在當代有了全新的注腳。57%的支持率,那絕非冰冷的數字,而是百萬家庭用溫暖的燭光拼成的璀璨星圖,映照出人民對他深深的信賴。在這個意義上,他比任何民調專家都更深刻地明白:真正的政治,是用皮膚去感知人民溫度的一門深邃學問。
地緣逐火,盜火之思
他,註定要在大國博弈的夾縫之中,跳起一場危險而又充滿智慧的探戈。
一邊接過北約遞來的標槍導彈,獲取力量的支撐;一邊警惕萬分,謹防成為大國棋局中的無辜祭品。在華盛頓的演講臺上,他收穫著如潮的掌聲,卻又時刻不忘提醒歐洲:“這不是我們的戰爭,而是文明的保衛戰”,言辭懇切,發人深省。
當美國國會為援助法案爭執不下,他如拜占庭的使節般,在麥卡錫與詹森之間巧妙周旋。他以如東正教聖像般的堅忍,靜靜等待著命運的轉輪緩緩轉動。
有人譏諷他是被人操控的“提線木偶”,卻未曾看到他如何將西方的有限施捨,精心煉製成自主的鋒利寶劍。在要求 F - 16 戰機時,他巧妙地將技術轉讓條款寫入協議,為國家的長遠發展謀篇佈局;在清算俄羅斯資產時,他堅定地堅持烏克蘭法官必須參與審判,捍衛國家的司法主權。這不禁讓人想起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在列強環伺的艱難處境中,憑藉外交的優雅舞步,為國家舞出生存的廣闊空間。
未竟史詩,歷史留痕
當和談的陰雲再次悄然籠罩日內瓦,他獨自整理檔的側影,被鏡頭精准地定格。那個瞬間,濃縮著所有抵抗者的孤獨與執著。他恰似加繆筆下的西西弗斯,明知巨石終將滾落,卻依然固執地為攀登賦予非凡的意義。那些將他的堅持稱為“豪賭”的預言家們,永遠無法懂得,對於身處戰爭漩渦的溺水者而言,每一根看似微弱的稻草,都可能是承載希望的諾亞方舟。
此刻的基輔,春雪正漸漸融化。在某個地鐵站裏,流浪音樂家奏響了《向日葵之舞》,悠揚的旋律在空氣中彌漫。琴盒上貼著澤連斯基戰前參演電影的劇照。人們紛紛投下硬幣,那不是為了祈求勝利的功利之舉,而是向某種超越勝負的尊嚴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我們正在證明,渺小不是宿命。”這部長達三年的戰爭史詩,雖尚未落下終章,但歷史早已在某個戰壕的黃昏,悄然寫下了公正的判詞。當演員摘下喜劇的面具,露出悲劇英雄的真實面容,整個時代都成為了他的宏大劇場。
遙想當年,項羽在營帳中對著烏騅馬與虞姬,那一聲歎息,何嘗不是一種孤獨的呐喊。他的孤獨,是英雄末路的無奈;澤連斯基的孤獨,是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為國家爭取生存空間的艱難。
角色沙盤,變換推演
五角大樓的晨霧尚未散盡,戰略沙盤上的藍旗已集體東移。那些曾插在基輔郊外的星條標記,正化作電子信號飛越國際日期變更線,在關島的珊瑚礁群間凝成混凝土工事。太平洋的浪湧吞沒了第聶伯河的槍聲,五角星紋章的戰艦犁開馬紹爾群島的碧波,銹蝕的標槍導彈殘骸卻在哈爾科夫農莊的雪地裏,長出野罌粟般猩紅的鐵銹。
白宮橢圓辦公室的地毯上,烏克蘭的求援信正被裁切成幾何模組。某個清晨,特朗普用鍍金裁紙刀將馬裡烏波爾的座標劃入碎紙機,紙屑飄落成東京灣軍演的電子圍欄。原該馳援頓巴斯的坦克,此刻正在沖繩碼頭卸下太平洋鹹澀的晨露;基輔街頭士兵們仰望的無人機空域,已然佈滿菲律賓蘇比克灣升空的偵察矩陣。
首爾龍山基地的探照燈下,《美韓共同防禦條約》正在褪色,新的條款在導彈試射的尾焰中淬火成形。日本列島化作巨弓,三菱重工的車間裏,射程突破憲法的箭矢正批量分娩。當雅加達會議廳的吊扇攪動濕熱空氣時,納土納群島的礁盤已植入美軍識別碼,如同古代水手在星圖上刺下的航海標記。
暮色中的安德森基地,F-35機群正在做起降訓練。它們的尾焰在晚霞中拖曳出藍黃漸變的軌跡,恍若被放逐的烏克蘭國旗碎片。而此刻基輔獨立廣場的銅像下,某個流浪藝人正用美制彈殼焊接風鈴,叮咚聲裏混著黑海與太平洋的鹹澀季風。當戰略家們在沙盤上推演文明興衰時,地球背面的軍港裏,生銹的錨鏈正將落日絞成兩半:一半沉入大西洋的記憶,一半熔鑄成太平洋的黎明。
午夜航班劃過華盛頓時,澤連斯基在舷窗中看到自己的多重倒影。他或許是流亡者,在異國他鄉為國家尋求幫助;他或許是殉道者,願意為國家的利益奉獻一切;他或許是賭徒,在國際政治的博弈中奮力一搏;他或許是戲子,但他的每一次表演都充滿了拯救國家未來的成分。
末路英雄項羽的失敗,是歷史的遺憾;澤連斯基當下的困境,多少是來自現實世界地緣政治風險夾縫裏的挑戰。
後記:出國前筆者用了近三年時間收集整理各種關於澤連斯基和俄烏戰爭的視頻與文本資料,作為中國教育學會的長期會員,本人一邊在為申報中國教育學會關於國防教育課題準備資料,一邊斷斷續續寫了一些關於戰爭話題的殘篇斷章。這是筆者關注澤連斯基以來陸續寫的一些關於他個人精神風貌的一篇縮微版散文,不完全代表筆者的政治站位和立場。

-
興大展現實踐「一所大學守護一條河川」的豐碩成果 NUST 跨校協作共創永續城鄉
2025-10-31
-
2025-10-31
-
2025-10-31
-
國資圖獲臺灣能源效率協會捐贈《國家地理公播網》授權 供民眾免費線上觀賞
2025-10-31
-
2025-10-31
-
2025-10-30
-
「改變從理解開始」中醫大附醫攜手世展會 「改寫她們的命運」影像展
2025-10-30
-
東海大學 許和捷教授 榮獲「114年第12屆教育部藝術教育貢獻獎-教學傑出獎」
2025-10-30
-
臺北捷運局《加蚋豐華》取得優先議價權打造加蚋站通風井X公共藝術
2025-10-28
-
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新任署長陳俊言 期許以國土保安為優先及構建新的農村發展支持體系
2025-10-28
最 新 資 訊
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