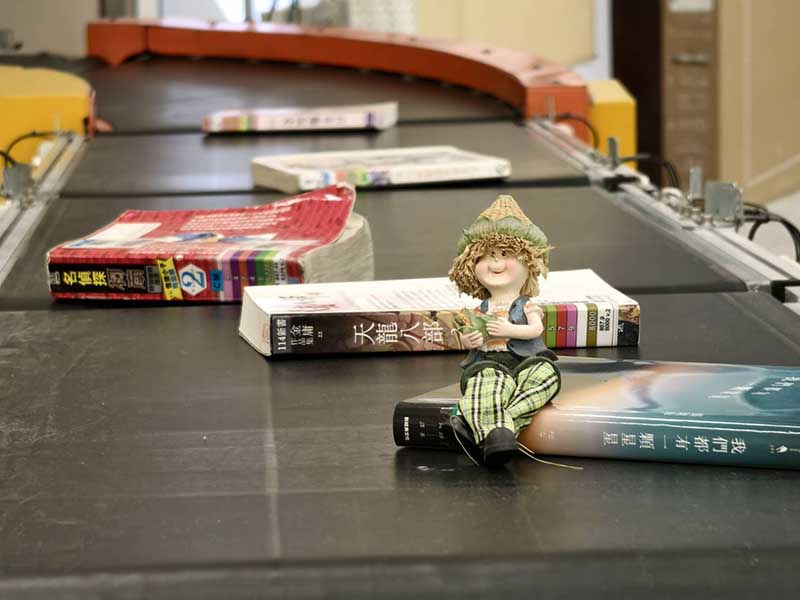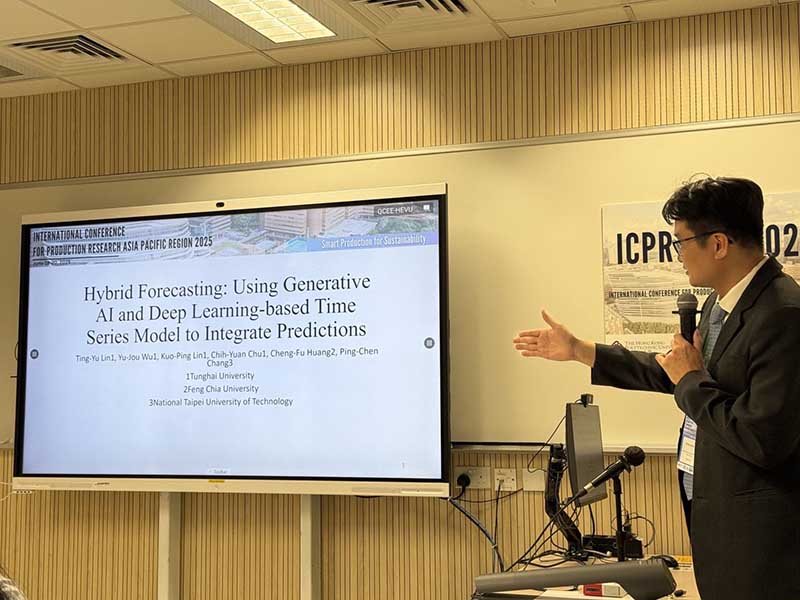WORLD CHINESE JOURNALISTS
百年前的北京大學,是一座正在冒煙的火山。言語是火,思想是火,青年人奔走呼號,把沉睡的中國喚醒。回望百年前急匆匆的文明轉身,留下了太多遺憾。
1919年的春天,北洋政府簽下賣國的《凡爾賽條約》,五四運動應運而起。青年怒吼,知識份子奮筆疾書,從街頭到課堂,從報刊到講壇,一股強大的激進主義思潮席捲而來。
這股浪潮的出發點,是愛國,是反帝,是啟蒙,是對於舊制度、舊文化、舊倫理的徹底反叛。在那個歷史轉折的當口,這種覺醒是必要的,也是勇敢的。但令人憂思的是,中國的現代轉型,卻從一開始就缺席了一個必不可少的維度:保守主義的聲音。
當陳獨秀舉起“民主與科學”的大旗,胡適提倡“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他們所對抗的,是中國幾千年積澱的文化與秩序。他們將“孔家店”視為腐朽的根源,將古典視為阻礙現代的絆腳石。怒火燒遍了傳統文化的每一個角落,卻鮮有人問一句:我們是否也燒毀了自己精神的屋脊?
在那個奔湧的進步浪潮中,少數幾位學者如吳宓、梅光迪、胡先骕、梁實秋,悄然站成了一道薄弱的堤壩。他們創辦《學衡》雜誌,試圖從白璧德、柏克等人的保守主義哲學中尋找出路。面對橫掃一切的激進主義,他們呼喚理性、自律、秩序與傳統。他們不否定現代化,卻反對以破壞為名的“重建”。
然而,這些聲音太過微弱,太過理性,也太不“革命”。在那個“救亡壓倒啟蒙”的年代裏,溫和理性者註定成為時代的棄兒。他們被稱為“保皇黨”“反動文人”“資本家的乏走狗”,最終沉沒在歷史的濁流之中。
從此,中國走上了一條極端激進、缺乏思想制衡的現代化道路。
精神病根與傳統缺席
思想決定國運。方向錯了,越努力,越偏離。
五四以來,中國確實發生了劇烈的變化:王朝制度瓦解,科舉制度廢除,白話文取代文言文,女性地位提高,民主、科學成為口號,西方的各種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實用主義如潮水般湧入。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陷入了另一個陷阱:“全盤否定傳統”的激進路徑。
這條路徑的隱患在於,它並不建立在充分的理解與整合之上,而是建立在斷裂與否定之上。傳統不再被視為可以傳承的文化資源,而是變成必須批判、清除的毒瘤。保守不再是一種審慎的思維姿態,而是落後的代名詞。
由此造成的後果,遠遠超出文化領域,深刻影響了中國的制度構建、社會結構、教育理念甚至人的心理結構。
我們可以看到,百年來,中國幾乎所有的制度設計都呈現出高度“工具理性”特徵,而缺乏“價值理性”的約束。從土地改革到大躍進,從文革到計劃經濟的徹底解構,從義務教育到“高考獨木橋”,一切都追求效率、力量、整齊劃一,鮮有對於個體、傳統、人性的溫柔與尊重。
保守主義講求“人是有限的存在”,需要制度與文化的節制。而激進主義相信人是可以被徹底改造的,因此常常越過底線,走向烏托邦。
從烏托邦出發的現代化,終將是沒有靈魂的高樓大廈。
再回頭看五四,令人最為痛心的,不是胡適敗給了陳獨秀,而是吳宓敗給了胡適——連溫和理性的自由主義都無法立足,何況更為深沉的文化保守主義?
這也就註定了此後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將極端而激烈,缺乏思想制衡與文化根基。中國的現代化,不像日本那樣在明治維新中保留皇室與神道傳統,也不像德國那樣在理性中吸納古典文化,更不像英美那樣在漸進中維繫古典自由主義傳統,而是一種脫胎換骨式的改造與重構。
這種文化傳統的“真空”,讓中國社會在進入工業文明後無法構建起穩定而深厚的倫理基礎。權力至上主義、技術工具主義與歷史虛無主義接踵而至,社會陷入價值混亂,民眾缺乏精神家園,國家缺乏文化黏合力。
我們不斷改革,卻始終改革不到“文化本體”之上。我們不斷發展,卻始終帶著“空心的靈魂”。這不是經濟的問題,也不是教育的問題,而是“思想根基”的問題。我們沒有保守主義,正如樹木沒有根。
精神的倒影與當代的鏡像
今天的中國人,站在高樓之巔,目睹燈紅酒綠的繁華,卻在內心深處感到前所未有的荒涼。
我們擁有全球最多的高學歷人口,卻缺乏精神判斷力;我們擁有全球最強的工業體系,卻缺乏文化整合能力;我們擁有龐大的官僚機器,卻缺乏審慎理性的治理觀。
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思想的缺席,尤其是保守主義的缺席。當我們重讀吳宓、胡先骕、梅光迪那些在狂潮中孤立無援的文章時,我們會震驚地發現:他們早已預見了這一切。
他們在1920年代就質疑“達爾文主義”對人文教育的侵蝕,反對將“科學萬能”推向極端;他們在呼籲“自由”,卻也警惕“自由”變成“無序”;他們在面對西方現代化的同時,也努力從中國古典文化中尋找靈魂之光。
他們不是拒絕現代化,而是希望在文化上有所承續;不是反對科學,而是希望科學之上還有倫理;不是討厭民主,而是認為民主必須紮根於教育、傳統與道德基礎之上。
這一種“溫和的現代化”,才是深刻的現代化。可惜他們敗了。他們敗給了時代的焦慮,敗給了輿論的狂熱,敗給了“革命即正義”的幻覺。他們的命運,成為中國現代思想史上最悲愴的一頁。
我們信仰技術,卻拒絕人文;我們加速發展,卻不敢反思方向;我們高喊“自信”,卻內心焦慮;我們宣導傳統文化,卻將其娛樂化、符號化、空洞化。我們創造了巨量的數據,卻無法回答一個最簡單的問題:我們是誰?我們要往哪里去?
這一切的根源,仍舊在於我們拒絕真正回望。五四運動以來,我們從未真正與傳統和解。我們要麼全盤西化,要麼盲目復古;要麼沉溺激進主義,要麼陷入犬儒;要麼高唱未來,要麼否定一切。
我們缺乏一種可以“既批判又尊重傳統”的姿態——而這,正是保守主義的價值所在。保守主義不是復古,不是守舊,而是節制、敬畏與延續。
它承認歷史的複雜性,尊重人性的有限性,也珍視文明的連續性。
在當今這個充滿焦慮與撕裂的時代,我們比任何時候都需要保守主義的力量:它或許不能帶來奇跡,但能防止崩塌;或許不夠激情,卻能穩住人心。
正如一位哲人所說:“一座沒有祖先的城市,只能建造廢墟。”
失根的教育:從“立人”到“制器”
若要解讀一個社會的思想深處,最直接的鏡像,便是它的教育。
中國教育百年來,一路追求現代化、科學化、標準化,培養了無數“聰明的機器”,卻越來越少培養“有靈魂的人”。教育之根本,應是立人;但我們卻在制度化的狂奔中,將“育人”異化為“制器”。
五四運動之後,中國教育逐步從傳統私塾過渡到現代學校體系,表面是進步,實則卻將古典精神的血脈徹底割斷。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四重人格構造,被削平為“考大學、找工作、掙工資”。教育的終點不再是“成人”,而是“成才”——一種對工具理性無上崇拜的投降。
在這條道路上,保守主義的教育理念無處立足。吳宓宣導“文學即人生”,希望學生在莎士比亞與司馬遷之間學會悲憫;梅光迪強調“通才教育”,希望學生既有科學知識也有精神涵養;梁實秋堅信“人格比知識重要”,認為教育最重要的是培養一個完整的人——這些理念,在標準化考試、績效化管理與功利化導向中,被冷落,被邊緣,最終湮沒。
今天的中國課堂上,充斥著刷題機器與排名焦慮,極少有關於“如何做人”的討論。我們可以製造晶片,可以建造空間站,可以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科研系統,卻培養不出懂得節制、審美、敬畏、沉思的年輕人。
失去了精神根基的教育,註定只能造就“智而無德、強而無魂”的現代人——這些人,也正是今日社會迷失、冷漠、分裂的根源。
如果教育不能培養“溫良恭儉讓”的人格,那它又何以安頓一個民族的未來?
儒家與保守主義融合:中國傳統的現代可能性
現代中國社會表面自信而高亢,實則極度焦慮與浮躁。凡事求快、求大、求贏、求顯赫,已成為一種主導性的文化心理結構。我們嘲笑“慢”,鄙視“退”,排斥“柔”,恐懼“弱”,凡一切講究節制與中庸之道的行為,都被誤解為“無能”“不思進取”。
而這種對“節制”的恐懼,正是缺乏保守主義精神所致。保守主義哲學認為:人之本性有限,社會之構造複雜,歷史之演進有其深層邏輯。過度干預、過度激進、過度自信,常常導致災難。節制,不是消極,而是一種深刻的理性,是對人類局限的清醒認知。
但中國當代社會恰恰反其道而行之。我們信奉“突破”而非“穩固”,推崇“速度”而非“厚重”,推銷“高效”而非“節制”。從城市開發到教育制度,從輿論風向到產業政策,幾乎無處不體現出這種“全速前進、永不回頭”的思維模式。
這是一種危險的文化傾向。沒有節制的社會,如同失控的列車,看似澎湃,實則步步逼近脫軌。節制之所以重要,並非是因為它束縛人,而是因為它守護人。它是高樓的地基,是航船的錨鏈,是文明的刹車系統。缺少節制的社會,將無法自省、無法修復、無法真正“回頭是岸”。
今天的中國,需要的不僅是新政策、新技術、新制度,更需要一種“放慢速度、回歸本源”的集體精神覺醒——而這,正是保守主義最珍貴的禮物。或許有人會問:保守主義本是西方概念,緣何在中國如此重要?它是否與中國的文化根性相悖?
恰恰相反,保守主義與儒家傳統精神,實有天然的契合之處。
保守主義強調歷史的連續性、人性的有限性、制度的漸進性、秩序的中心性,而這些,正是儒家精神的核心。儒家的“中庸之道”“禮樂制度”“修身為本”“敬天愛人”,本質上就是一種文化保守主義。孔子之道,並非革命之道,而是延續、溫潤、克己、約束之道。
吳宓等學衡派人士的嘗試,其實正是在架構一種“中華版的文化保守主義”——他們既吸收了白璧德等西方保守思想的精粹,也深知中國傳統的厚重與底蘊,試圖在兩者之間建構橋樑。這種努力,雖未成功,卻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思想遺產。
可惜,主流中國現代化路徑選擇的是與儒家“斷根”——以“批孔”“打倒祖宗”為榮耀;而非“整合”,非“再詮釋”。如果我們今天重新看待儒家,不應將其視為封建餘孽,也不應囿於廟堂道學,而應將其視為一套深邃的文明體系——它提供的是人與人之間溫潤的秩序,是教育的倫理根基,是治理的柔性智慧,是精神的庇護所。
在一個日益物化、功利、躁動的世界中,或許儒家與保守主義的聯姻,才是真正屬於中國的現代性出路。
文明的回望,未來的可能
回望百年風雨,中國人嘗試過激進、嘗試過左傾、嘗試過徹底西化,也嘗試過民族主義的灌注,但我們始終沒有認真地走過“文化自省、節制發展、融合傳統”的道路。這是我們思想的病根,也將決定我們的未來命運。
如果說文明是一條長河,那麼保守主義就是那條河的堤岸,它限制奔流,卻保護河流不至氾濫;如果說社會是一座大廈,那麼保守主義就是地基,它不顯眼,卻決定了整座建築的穩固與壽命;如果說國家是一棵樹,那麼保守主義便是根系,它藏於地下,卻供養了整棵枝繁葉茂的生命體。
今日之中國,早已不缺速度、效率、規模、技術,但極度缺乏節制、教養、敬畏、持重。我們需要再一次,靜下心來傾聽那被掩埋百年的聲音——吳宓的低語、梁實秋的獨行、胡先骕的沉思。他們雖已沉默,卻依然在時間深處發光。
這不是復古,也不是退步,而是一次文明的回根之旅。
當我們能在高樓林立的城市裏,重新讀《論語》;當我們能在火箭升空的時代裏,仍能尊重“慢工出細活”;當我們能在民族自信的呼聲中,仍願低頭向傳統學習——那時,我們或許就真正告別了“五四之後的失衡”,走入了一個“既有速度也有溫度,既有自由也有敬畏”的中國現代文明。
而這一切,就從再度讀懂“保守主義”開始。也許,我們不必再重演百年前的爭鬥,但我們可以在今天,為那場未竟的思想之爭正名。願我們能在五四的激進背後,看到吳宓的沉默;在“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後,聽到梁實秋那句:“生活是細水長流的詩”;在新時代的高樓中,找回“可以讓心靈歇息的廟宇”。
只有這樣,中國的現代化,才可能真正走出“曲折探索”的命運,找到一條既紮根傳統、又擁抱未來的道路。
-
慶祝法寶節 惠中寺舉辦2026年「人間有情‧佛光有愛」陪伴弱勢家庭溫馨迎接新年
2026-02-02
-
慈濟在台灣各縣市舉辦冬令發放暨圍爐活動 邀請周國進先生分享人生新價值
2026-02-02
-
2026-02-02
-
興大(質譜AI中心)」正式揭牌 產學攜手 推動農業永續與國際競爭力
2026-02-02
-
打造深度與前瞻性的科普學習平台 中山醫大與科博館共同主辦「第30屆高中生生命科學研習營」
2026-02-02
-
邀請全民走春喜迎馬年 國美館「丙午躍春─藝起探春」春節系列活動開跑
2026-01-30
-
2026-01-28
-
2026-01-27
最 新 資 訊
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