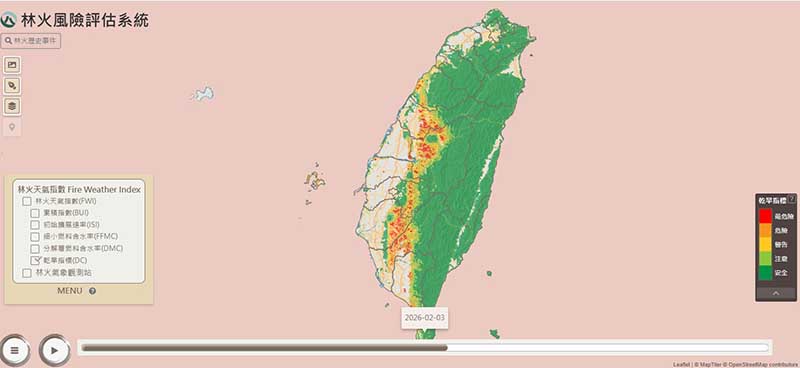WORLD CHINESE JOURNALISTS
相信用手中筆講述澳門抗戰故事的時候,吳志良先生深情默默挑燈伏案,鹹澀與酸楚一定模糊過他的視線。不然,為什麼作為讀者的筆者,怎會感同身受地止不住淚落衫襟。
這篇三千多字的厚重文本,敘述的大都是小人物的小故事,但小故事卻蘊有千般氣象,藏著萬鈞之力!試看帶入感極強的畫面:1941年聖誕夜,近在咫尺的香港遭日軍佔領前夕,一個木盆裡繈褓中塞著求救片紙僅三個月大的孤嬰——父母于跑馬地橫遭日機轟炸慘死的最小無辜者,希望好心人能收養。這祈求,隨著海水波浪的顛簸,向讀者的眼前鳧遊而來。這開篇,這沒有被蔣兆和緣寫進《流民圖》而遺憾的畫面,任誰人見了會不心傷動容?
相比香港的這般慘境,再對照祖國大半陸沉殤痛,澳門倖免於難是多麼的奇幻:日寇的鐵騎愣是沒有蹂躪至此。傳說那筆巴西與澳門棋局盤面上普通生靈的實空交換,讓多少中國人因為避入澳門小城而免遭塗炭。而未遭兵燹火焚的澳門,他的幸運與新生,已在街巷里弄絲樣柔軟輕搖的煙火中。
絲紋密絡,會織出錦繡神州,弱微涓滴,也終竟會呈現蒼茫浩蕩!
澳門,在吳志良先生的筆下,歲月鮮活。
只是,通過小人物的故事講述,多了難以數清的生動傳奇。
中山的疍民,嶺南大學的教授,上海青幫大佬的姨太,白眼塘街“義學收容所”的年輕陳姓女子、潮州阿嬤、上海小姐、風月場舞女、緬甸歸僑林叔、上海裁縫王太太、巷尾中山農民老陳、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兆麟和學生李秀蘭……
隨著怯弱屑小的各色人物渡海湧入,澳門一瞬間熱鬧起來。就如吳先生的娓娓述說,筆者牢牢記住了這樣的資料:至1942年春,澳門人口從17萬暴增至50萬,每平方公里承載著比加爾各答更密集更強烈的求生欲。
在吳先生的講述中,筆者從諸多的故事裡,讀得四個字眼:殘暴——慈愛!
殘暴,是被樁樁件件的事舉側面佐證出來的。日本軍國主義對亞洲尤其對中國的冷血殘忍,決是罄竹難書!
小城澳門舉島展開的救濟、支援、互助、團結,共同繪就一幅人人自覺博愛慈心悲願世相圖!而所有的善良付出,成就的絕非市井煙火,分明隱含有大美愛憎!這便是,將對日寇的仇恨,表現在對流離而來的生命救濟中,表現在對前方與日殊死作戰竭盡全力支援的行動中。
於是,還原發生於澳門在地五年間的故事,每一頁發黃的記憶,都成為融入民族傷痛揮之不去的堅硬標識。
吳先生輕輕剝開歷史塵霧:澳門某女中學生、媽閣廟廟祝林德、瑪利亞方濟各修女,崗頂前地葡人別墅玫瑰園種蔬菜的主人,他們紛紛加入到大愛無悔的“義”的行列。當然,還有嶄露頭角的在地知名人士何賢、高可甯、柯麟、傅老榕……當然,還有澳門四界救災會的青年們鑄就的“海上生命線”、五桂山遊擊隊、東江縱隊那出生入死的蓬蓬青蔥……這一切的一切,一再闡釋出這樣一條真理:中華民族不會亡!
先聖有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各色人物的默默行為,無言大美,必得有一個中肯評述——幸已流瀉于吳先生的筆端。
吳先生的講述仍在繼續,作品裡,讓我們感動之處實在太多。
概率而言,文章以卷軸展開的書寫樣式,看似無有繩墨佈置,卻盡顯自然高格,讓人感到壓心的沉重。五卷本的敘述,每一卷都似在探尋並豁開島城眾生人性善良的根底。渡海、共命、暗線、微光、星火,每一卷,都在高度凝煉又生動傳神中獨立成篇又都用“慈愛”相系,歸於悲愴美!
綜觀全文,也讓人品味出韻律節奏之感。這韻律,已非池塘春草謝家春,而是真與善的契合,加上吳先生的才情,以及他一貫的志趣,致臻真正的美爆。想這也是來自於他長期耕耘澳門,養成對澳門無與比肩的深摯情感,即大仁大愛從而倉中儲粟,豐滿實在,運用起來信手拈來的原由。
而結尾終章,再次點題,澳門的慈悲大愛,並沒有隨時光流逝而散去,他們正在恒長延伸,從基因的譜系中,成為澄明暉光,悅耳琴音。于此,筆者終於明白吳先生串綴起來的小故事聚合為磅礴力量沖決日寇殘暴的苦心,終於明白抗戰最關鍵焦灼激烈時候,澳門人人參與抱薪添火焚毀日鬼狼子野心的作為。一人一個故事,共同撐持了澳門慈悲大愛的天空。
馮友蘭先生曾有言:“好的藝術作品,不但能使人覺其所寫之境而起一種與之相應之情,且離開其所寫,其本身亦即可使人覺有一種境而起一種與之相應之情。”讀吳先生作品,亦複如是!筆者還想,憐惜普通生命,才有以淒厲之筆,書寫出斷腸之句,才有字裡行間,溫厚之氣撲面,雄偉、遒勁之色盈心。
閃回到文本開頭,那個木盆漂至澳門的孤嬰,早已成為中華民族骨血的象徵。由此,我們致敬這部澳門抗戰彌足珍貴的文存。
-
陪伴移工迎新年安心轉職!中彰投分署114年成功媒合逾2,000名移工銜接新雇主
2026-02-13
-
2026-02-13
-
思索人與自然共生的可能 科博館植物園推出《野地之詩-臺灣原生草花的棲地記憶》特展
2026-02-12
-
邁向新階段農業學術研究與人才培育合作 興大與農業試驗所簽訂(MOU)
2026-02-13
-
2026-02-12
-
農曆年節送禮不煩惱 工策會官方認證「臺中市十大伴手禮」市民安心選擇
2026-02-11
-
創世「第36屆寒士吃飽30 送禮到家」公益行動讓凜冽寒冬充滿愛的味道
2026-02-11
-
開創醫療檢測與精準分析的里程碑 興大奈米團隊獲得日本光電大廠高度肯定
2026-02-11
-
臺灣高等教育資源共享與區域均衡發展上邁入新階段 國立大學系統擴大至15校
2026-02-10
-
助600位弱勢新住民二代翻轉未來 賽珍珠基金會「童心協力」圍爐20年愛不間斷
2026-02-10
最 新 資 訊
NEWS